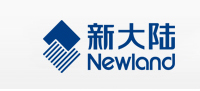浙江省青坑村更香有机茶业公司俞学文代表带着小微企业的“痛”来到北京:融资之“痛”、人才之“痛”、税负之“痛”。对于小微企业来讲,这是绕不开的三道“坎”。
“我感受很深啊。”俞学文深有感触地告诉本报记者。更香茶叶,由俞学文与妻子创立,主要生产、经营有机茶业及相关制品。这家科技型企业跨过了“微”的阶段,但尚属小企业,“小微”的苦痛依然困扰着俞学文。
融资之“坎”:“不是融资难不难的问题,是根本融不到”
“小微企业融资难?不是融资难不难的问题,是根本融不到!”联系到自己的经历,俞学文说,“小微企业有什么?没有地位,没有品牌,没有基础,去哪里融资?”
济南市工商联副主席于晓玉代表有着类似的遭遇。她最近正在帮一位做化工的朋友贷款,“很艰难,已经办了两个月了”。
“贷不到(款)!银行不给他钱。只因为他是小微企业,就不去理他。”傅企平代表,同样来自浙江企业,他为本报记者讲了一个小微企业被高利贷“逼死”的故事。
当地一家“小微”向银行求助时,因为“三无”,即“无地位、无品牌、无基础”屡屡被拒;无奈之下,公司只得求助于“高利贷”,费了“九牛二虎之力”,背上了沉重的“包袱”。后来,遭遇国内外环境变化,这家“小微”最终“倒下”。
“如果当初银行贷给他款,如果当时国家给予"小微"优惠政策,可能会是另一个结果。”傅企平很惋惜,但世界上从来没有“如果”。
“小微企业往往规模小、底子薄,提供让银行满意的担保是很难的,让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又会增加融资成本,甚至还要求反担保。”于晓玉代表认为,银行的不信任和苛刻条件,为“小微”设置了一道绕不开的“坎”。
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委员提醒“不要都指望商业银行”,“税收和财政政策应该给中小企业创造宽松的环境,但更关键的是要金融领域改革,打造政策性的融资机制,给小微企业"输血",不要都指望商业性银行能持续不断地支持中小企业。对于小额贷款公司这类民间金融机构,应该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,政府应当对其注册资本金、监管手段、风险防范等给予必要指导”。
但民间借贷的高成本,加重了小微企业的负担和发展风险,一旦外界环境变化,又如何承担?
人才之“坎”:“他们宁愿拿国企的1500块,也不愿拿小企的4000块”
“这是小微企业面临的最大难题!”缺乏人才,难留人才,成为俞学文眼中“小微企业绕不开的最大"门坎"”。
“小微企业人才严重短缺,管理人才、科研人才都缺。”经营“小微”,让俞学文对人才缺乏有了更多认识,“现在很多大中型企业都出现"用工荒、用工难",更何况"小微"!”
“留才难”和“引才难”,成为小微企业的双重难题。
“现在整个社会都浮躁,尤其是大学生。你想想,一年换五份工作,工资先不说,你能为五家单位做出什么?”
“第二,社会导向不对。一个公务员岗位,恨不得有一万人报名。他们觉得进了机关,就端住了"铁饭碗",就进了"天堂"。”
“还有都往国企涌,就是进去扫地,他都愿意;他进国企只拿1500元工资,都抱得紧紧地;而小微企业,你给他4000元都不来。”
不过,俞学文也明白,“小微”因为抗风险能力低,给“人才”造成的不安全感,并不是收入的落差能弥补。
在“留才”与“小微”发展之间,傅企平则算了一笔账,“如果在工资、奖金、股金等待遇方面给予人才稍高的待遇,这方面的投入就高,用于公司发展的投入就少了,再加上"高利贷",公司的利润从哪里来呢?”
税负之“坎”:“一半多的利润都缴了税费,拿什么发展?”
税负之“坎”让小微企业难堪重负。
“沉重的税负也压缩着小微企业的利润空间。”傅企平坦言。此言不虚,两会期间,福建新大陆集团王晶代表曾给本报记者算过一笔账,显示小企业“赚得少交税不少”的现实。
除了“17%的增值税、25%的企业所得税”等应缴税种,还有教育费附加、水资源费等名目的“费”。“通常交1元税,要交0.5—0.7元的费。”
按照她的计算结果:“按100万元营业收入计算,我们的利润是10万,但要交近16万的税费”,“一半多的利润都缴了税费,拿什么发展?”采访中,一位匿名的小微企业代表反问。
实际上,俞学文代表也承认,近两年,从国家到地方都采取各种措施,对小微企业进行减税。他关注的是,“国家政策今天出台,不可能明天就见效,没那么快。”
而在高地价时代,小微企业对土地的需求难以满足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。“小微企业的用地,就很难得到满足。”傅企平说。
去年,本报记者采访山东某小微企业。一台总重量达900吨的重型压机正摆在公司局促的小院里。“厂房里盛不开了”,企业负责人说,“批地申请已上交近一年,跑了几趟没有回音”。对方郁闷地说,“相对大企业,我们的交税就是少,那怎么办?”
跨越三道“坎”:要从财政、货币、产业结构等方面支持
融资、人才、税负,小微企业面前的三道“坎”,似乎难以逾越。众多代表并不这么认为。
浙江工业大学经管学院程慧芳代表认为,“中小微企业融资难,可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法律保障来解决。”
“目前,银行结构是大银行多,能够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小银行数量不足,加之中小微企业交易成本高、信息不对称、经营风险较大,使其在信贷筛选中处于不利地位。我建议,应该在法律层面上出台一个"中小企业具有信贷机会均等"条款,不管金融机构是大是小,都要对中小微企业提供相应的服务。”
实际上,梳理小微企业的三道“坎”,“融资难”问题可谓是解决后两个“坎”的突破口。毕竟,对小微企业来说,有了钱便有了实现跨越的资本和可能。
而在减税方面,国家已出台的措施包括: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;将小型微型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;对小型微型企业三年内免征部分管理类、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。
本次两会期间,就小微企业的减税问题,代表委员们纷纷给出建议。
据《光明日报》报道,日前,15名人大代表、14名政协委员联名建议,为提高中国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,要抓住当前我国财力充足的时机,通过适度减税,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资金负担,推动转型升级,帮其渡过难关。
在政府和相关部门努力之外,小微企业自己也要“主动”起来。“有些政策不会自己找到你手里,要去沟通,要去争取。”俞学文代表建议。
今年,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几次提及小微企业,要从财政、货币、产业结构等方面支持小微企业发展。
这让俞学文们多了几分信心。